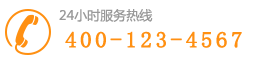
产品中心
PRODUCT

电 话:0898-08980898
手 机:13877778888
联系人:xxx
E_mail:admin@Your website.com
地 址:广东省清远市
从“占卜感性”“占卜理性”到“占卜德性”
④林忠军《易学源流与现代阐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
夫子经由《周易》,穿越《周易》,又超越《周易》★★★,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其最重要的超脱就在于★★“道德理性”的升华,这也就是★“由巫到仁”的历史转化。实际上,这种“化巫为仁”乃是历史积淀的产物,需要从经验到先验的累积沉淀★★,仁始终没有逃弃由★★“巫通”而来的与天地的沟通,始终是现实人们所要遵循的德之“道”★★。“巫”贯通天人★★★,“史★★”延续古今★★,或者说,巫与史有差异,“巫”使得天人合一★★,“史”则让历史延续。(14)巫史传统的“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及其合一,恰为★“占卜德性”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中国人的★★“情理结构★★★”也由此而生,《周易》对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确实功莫大焉。
《周易》体现了一种华夏远古的★★★“占卜理性★★★”,“占卜理性”的独特说法来自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他从思想发源的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及文字差异:★★★“中西文化间有着深度的不同★★,两者尤因表意文字与字母文字相去甚远而相异,其对立之源在于,中国一方★★,思想最初以一种极为讲究的占卜方程式为导向★★,希腊-拉丁与犹太-基督教一方,思想最初以宗教信仰为导向。★★★”①这里所说的★★“占卜方程式★★”是西化的说法,但占卜被★★★“程式化”的确有赖于中国人对理性力量的使用,由此★,汪德迈提出了中国独具的“占卜理性”概念★。
知《易》行《易》要得以实现,那么★,对《易》的知就不能只是“认知★★★”,更要有“感知”★★★,前者是(知★★★“道”的)“占卜理性★★★”,后者是(“感”通的)★★“占卜感性★★★”。而且★,这个“占卜感性★★”趋成了《易》之美学,因为在西方原本的语境当中,“美学★★★”(aesthetics)的本意就是“感性学”。以往的《周易》美学研究深受宗白华的影响而更多从“象”的角度入手,但其实可以拓展开来,转而从“占卜感性★★”直接入手★。从更广阔的思想高度观之,这种“占卜感性★★★”并不像“占卜理性★★★”那般可以直接归属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而应归之于“实用感性”的历史发展序列之内★。
的的确确★★,古人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乃是知行合一的,这要追溯到远古的占筮传统那里★。关于易学史上的★★★“两派六宗”及其演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就象数派而言★★,汉初易学所讲的象数尚与古法接近,焦赣★★★、京房等人的象数易则大讲天人感应、占验征兆。到了北宋的陈抟、邵雍那里,象数易学得以再度兴起★★,他们凭借自己开创的河图洛书、先天易学来探究天地宇宙的奥秘,于是《周易》不再贴近民用。就义理派而言,魏人王弼彻底罢废了此前两汉象数易学的思路★★★,而用老庄思想解《易》★★,北宋的胡瑗★★★、程颐则借《周易》来阐明儒家思想,南宋的李光、杨万里又援史入《易》。表面上看,象数派更接近于★★“用”派,义理派更接近于“知”派★,但无论两派还是六宗,其实都是知行合体★★,只是偏重不同而已,因为中国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即知即行的★“实用理性”★★★。同时,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即觉即感的★“实用感性”参与其中★。
从《周易》智慧的思想深层出发★★,笔者认为,仅仅关注中国人的“占卜理性”是不够的,与理性相对而出并与之融会贯通的★★,还应有一种“占卜感性”,而且“占卜感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居于★★“占卜理性”之先的★。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交融统一★★★,尽管我们在做出如此划分之时,感性与理性已然被割裂开来,但是中国智慧恰恰达到了二者的阳阴互动与动态平衡。
我们可以从外在天地与人自身两方面来看待“神★”:一方面★,古人“神明”的本义乃指“天与地之间的交通过程,进而衍化为天地之间最重要的媒介★★,成为天地之间的气化主宰者,成为造物‘生机★★’之源”⑤。在易学思想里★★,神明与阴阳也有★★★“德★”与“体”之分:★“神明系天地分合其‘德★★★’之过程★★,也是未分定各‘体’的状态★★;而阴阳两仪,则分合天地之现象与形体……‘神明’可以说是一种★‘宇宙一体’的状态。★”⑥但另一方面,感通的主体仍是人★,“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周易·系辞上》)★★,圣人更能“见天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系辞上》),由此方能够“继志述事”,从万物生生见天地之★★“志”★★★,从阴阳妙合见天地之“事”。所以说,“易道寂感之神★”★,★★“非人格神之神★★★,亦非从气而言的神★★,而是从天道易体神感神应妙运生生而言之”★★。⑦于是,所通之★★“神”便超越了主客,从而达到一种★“妙万物★★”而“穷神知化★★”的美境。这种美化的境界恰恰是由“占卜感性★★★”而非★“占卜理性”生发出来的,因为中国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恰是这种妙合之化的★“神化境界”。
我们再以占卜的感性、理性与德性的三维结构来反观整个易学史的发展。在易学史上★★★,“象数派★★”尽管凸显符号化,却更倾向于数字化的★★“占卜理性”,同时也注重以形式呈现的“占卜感性”;★★“义理派★”则以道德化的★★★“占卜理性★★★”为主而以融情入理的“占卜感性”为辅。这从邵雍和程颐的释《易》张力当中就可得见★★,但是象数与义理两派到了宋代又皆重孔子所开创的★★★“占卜德性★★★”★★。“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统一,恰恰有赖“占卜德性★”之整合。有趣的是★★★,到朱熹那里,似乎又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周易》侧重卜筮性的维度,这是巫史传统在易学发展史上不断隐现的现象,说明巫史传统始终未断,但《易》在朱子那里终究是服务于“圣人之道★”的,也终归于★★“占卜德性”★★★。
质言之,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则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才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贡献。
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1)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易·系辞上》)《周易》本身既是没有“思★★”的,所以无法与之“思通”,也是无有★★“行”的★★,所以就需要人经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周易·系辞上》)的理性与感织的活动,如此才能★“通其变”从而成就天地之文。因为君子既有★“为”也有★★★“行★★”★★,他们在筮占过程当中沟通天人,从而达到“其受命也如响★★★”的通达之境。当然,这种通达并不是人与天的“直通★★★”★★,还需要以蓍草这样的“神物”为中介,★★“极其数”★,定卦象★,★★“遂通天下之故★”,这就不是“占卜理性★★★”所能达到的了,“占卜感性”在其中同样发挥着核心的功能。
汪德迈将这种理性逐步成熟的历史联通过程描述为:“该理性运作首先完成了从原始骨占到龟卜占的转变,进而是龟璺规范成卜,之后从卜形变数到筮占数字★,最后应该是从原数字卦成为易经之重卦。★★”(《占卜与表意》★,第63页)这位汉学家同时关注占卜与表意两种理性的相互推动与逐步成熟:“甲骨文字之所以突然如此精密,仅乃因为占卜科学的水平高端★,表意文字的发明是其发展的顶峰★。同样,卜片上出现数卦原型,不能将之简单地解释为伏羲深化中的原始筮占,在殷朝时代突兀地出现★★,它的出现是占卜科学理性向数字理性的过渡的标志。”(《占卜与表意》,第64-65页)由此,数卦原型向“易经数卦原型”的转变,就被视为是在★“理性化运作”中延续完成的,这个判定是很准确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③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7-598页★。
关于《周易》与孔子的关联★★★,经学时代似有定论★,民国之后又新见迭出★★。2018年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中印思想对话国际论坛开幕后留墨宝的过程中,致力于“易学本体论★★★”建构的成中英写了上联的四个字——“知《易》行《易》”,然后就执笔停在半空★★★,问笔者下联该如何来对,笔者当场确无灵感未能及时应答,返家后脑海里却突现下联——“欲仁至仁”★!
经由《周易》而生发的这种天人“感通★★★”★★,不仅要感而★“通★★”之,而且要通而入“神”,这就指向了更高的神“通”境界★。“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易·系辞上》)感通进入“神★★”境,就是人之神与天之神内外通之,“往来不穷谓之通”★。这种神而“无方”所独具的能动性★★,大概不是“占卜理性”所能规制与束缚的,而是具有了某种感性化的自由性质与维度。由此,★“占卜感性”就诉诸人与《易》的交感,它可以知★★“几”入神★★★,在把握★★“成天下之务”的几微基础上,进入一种“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通“神★★★”境界。
实际上★★,在用《易》中得以凸显的“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皆来自更为久远的★★“巫史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的“情理结构”。或者说,中国人“情理合一★”的文明根源,其实在于巫史传统的历史塑造★。汪德迈也意识到了这个历史性根源:“在占卜成为科学性占卜学,宗教成为礼仪体制的同时★★★,萨满古老的舞蹈也转变成一种《诗经》的颂舞礼仪★★★,该礼仪从其迷人的跳神原型中继承了一种通感力,礼制开发了它,同样★★★,文言从其占卜原型继承了一种阐释力。”(《占卜与表意》,第40页)这就是将★★“宗教礼仪化★★”转化成为★“完备系统的文化机制”。这个历史转化过程,我曾归纳为巫的理性化、政治化与文明化的过程⑧。其中所说的★★★“通感力★★”就是巫通天地的“内通”,它更关乎“占卜感性”而非“占卜理性★”★。
(12)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151-152页。
汉字是否与占卜共生,或者汉字是否源自占卜,是个历史问题。汪德迈的独断也在这里,他反对下面这样一种架设:“存在一种早于甲骨文的文字,没有它,就无法解释甲骨文的绝伦精密。”(《占卜与表意》★,第62-63页)占卜官的确会造新字,但在他们扩展文字之前,也许从★★“结绳记事”时代开始,汉字就孕育了,只是后来在占卜当中得以广泛运用与极大扩充而已。但是★,这种中国文化的抽象化之理性过程,的确是占卜活动带来的(文字是人类理性的显现而理性并不仅以文字为显现)★★,这一方面源自技术操作上的“实用理性”,由此理性才成为践行的;另一方面则是将万物抽象为符码的抽象理性使然,由此理性才成为知性。
本文聚焦的历史问题是:易学智慧到底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情理结构”?或者说,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文化心理结构”受到了《周易》多广抑或多深的影响★★★?
(14)李泽厚★★★、刘悦笛《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⑩倪培民《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载《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
《周易》所讲求的“感通”,亦即★“感而遂通”★,就是中国人“占卜感性”的深度显现★★★。当然★★★,这种感通必先有《易》之“象”本身的感性显现作为客体对象★★★,但是更关键的还在于人作为主体如何与之感与通★★。因为所谓“‘通’就是人与易文本交互渗透、融为一体,文本内涵的天地万物之道★,与人性及其原有的观念吻合★★,而显现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换言之,人的内心世界思显现的正是文本中的那个★★★‘显诸仁、藏诸用’的道,人心与文本互显互诠★★”。④显然,这是一种从现代阐释学视角出发的阐发★★,但阐释学更偏重于思想的理性阐释★,而《易》之通却不是“思通”,是“感通★★★”★,这个感就是感性之★★★“感”。
⑨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在“实用理性”与“实用感性★★★”合一的大背景下★★★,占卜的理性与感性的融会贯通跟夫子与巫史传统的勾连有关★★:一方面,儒家思想有来自巫史的渊源,这一点笔者深受李泽厚相关思想的启示。当然他的“由巫到礼★★,释礼归仁”还注重以“礼”为中介⑨★★★。但另一方面,孔子开始走出了巫史,从而与“巫史传统”形成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关联★。这就是孔子“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的深意所在,它形成了一种当今学人所说的“如在主义★★”:它“既非有神论,亦非无神论,更不是怀疑论或者不可知论。它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神是否真的存在★★★,因而也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参加祭典、去进行精神性的活动”⑩。由是观之,如在,不是不在★,而是“如”其所在,实在却“如在”。那么,孔子是如何实现这种“如在主义★★★”的呢?这便关乎孔子与《易》的问题。
摘要: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贡献。实际上,晚年孔子知《易》行《易》所实现的“化巫为仁★”乃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仁始终没有逃弃由“巫通”而来的与天地的沟通★★★,但始终是现实人们所要遵循的德之★★“道”★。“巫”贯通天人★★,“史”延续古今,巫史传统的“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及其合一,恰为“占卜德性”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周易》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确实功莫大焉★。
夫子的自我表白——“《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是孔子研《易》用《易》的核心要义★。据张政烺的校注★★★“言关于易学,我以祝卜为后,而以德义为先”(《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第167页),这一先一后的顺序,恰恰显示出夫子的独特易学观:德先卜后★★★,德在卜前。尽管孔子并不否定卜筮,但他“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不仅拿《易》来占★★★“用”,而且以“辞”的内蕴为乐,于是进入到《周易》的思想深层。从“祝卜★”到★“德义”的转化★★★,正是孔子的★★“如在主义”。既不否定卜筮★★,又认为它在祝卜之后★,并从《易》中“观”到了德义★★,这其实是把巫道德化乃至文明化,上升到“德义”的道德层级,从而近于“仁★★”境。
作者简介★: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100732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辽宁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早年不识《易》、不认同卜筮到晚间深知《易》、接纳占筮,反映了夫子逐渐★★★“成人★”的过程。从理论上说★,夫子对经典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晚年反复研读《周易》之所思所得更接近于《易》的本质★★★。从践行上讲,晚年孔子周游列国而颠沛流离,对于命运无所把握时用《易》来测度未来,这也是符合情理的。“韦编三绝”的反复玩味,甚至被《要》篇描述为★★★“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般的热衷,也使“老而好《易》★★”抑或“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形象得以呈现出来★★★。
⑧刘悦笛《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中国文明起源的“巫史传统”试探》,载《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要》篇所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何★★“祝巫卜筮其后乎”,夫子对于祝卜与巫筮的态度昭然若揭★★。★★“德行焉求福★”,★★“焉”义为“乃”(《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第167页),即行德就是求福。祭祀是为了求福★,君子当然也求之★★,不过★★,以德行之★★★,福自然也会来。可见★,中国人较早提出了“德福一致”的问题★★,尽管现实中二者的统一往往不能达到牟宗三意义上的那种★“圆善”高境(15)。行了“仁义★★”,就不必多用卜筮了,这其实就是夫子的“如在主义”★★★。在对待巫史传统上,夫子采取了一种“祭神如神在”的态度,这正是中国人“一个世界”的大智慧★★。尽管祈神敬神,却并非彻底拜倒在神之下★★,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得以“成人”是以“仁”为内核的道德理性使然。
进而,从★★“明数”到★★“达德★★”★,就是达到了“占卜德性”★,而这种德性当中包孕着占卜的感性与理性双重成分,脱胎于二者又超越了二者。如此,“占卜德性”不仅从“巫”中而且从“史”中脱胎出来★★★。占卜当中“史”的原本历史角色不囿于“明数★”而升华为道德时,那就实现了从“史”到“伦理”的根本突破★。这种道德升华★,既是从“天道”而来的,更实现了一种★★★“人道”的突破,或者说,从★“天道”贯通于“人道”★★,由“人道”实现了“天道★★”★★,中国人的天人智慧得以由此尽显。
究竟何为★“占卜理性”★★★?这恰恰关乎中国占卜学精神本身的崛起:“占卜理性的精神,它把现象世界的无穷偶合化为几种格式化的、付诸计算的知性。这一精简过程是抽象化的过程★★:‘卜’的类型化是对无数未设定的卜兆的抽象★★★。而这里,史前泛中华文明在该阶段所独有的努力★★★,其特征是,在文字产生之前,抽象化是通过技术机制化进行的。卜兆的标准化工作是理性化的媒介。这是一种先进的★★、足以为中国表意文字之创造开辟道路的理性。”(《占卜与表意》,第15-16页)按照这位汉学家的解读★★,中国文字在占卜工具化制作的过程中才产生:“文字的创造自然是占卜官的事,占卜官从事造字★,完全在占卜理性这线条上★★★,占卜理性是中国占卜学有所演进的基础。★★★”(《占卜与表意》,第49页)我基本赞同此种★★“占卜理性★★★”的构想,并以之为华夏占卜学的思维根基之一★★★,但是不赞同这种中国文字晚起说★。
(11)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9-16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载《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总之,从知《易》行《易》而来的道德意识★★,并不是纯然的伦理理性化★★★,其中必然有道德的情感浸渍其中,这就是中国人的“情理结构”★★★。道德之情与道德之理乃是合一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由此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这种智慧在晚年孔子“以《易》求德”那里就已经被开启了。
然而★★,汉学家的另一个判断却可能是接近史实的,那就是认定甲骨占卜与八卦原型之间具有更深层的关联。这种关联最早的发掘者是古文字学家张政烺,他在1977年吉林大学古文字讨论会上就富有洞见地指出,不仅“铜器铭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而且陕西岐山县出土的卜龟当中,“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中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繁,只是阴阳二爻”。而且,分析29个不同器物残片上的32条数字格式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数字格式只能从蓍草占卜的雏形意义上来解释,他还对这种筮法加以初步蠡测并认定占卜已经从国之大事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了。②这种研究已显露出从远古占卜到《周易》八卦的历史绵延性,《周易》是★“占卜理性★★”的某种主流结晶。关于与乾、坤卦名有关的商周古文字的近期研究也证明《周易》的★★“爻辞★、卦辞与甲骨文一样是记载占卜成果的文字。卜骨与卜筮是不同的占卜方法,但是无论什么卜法,占卜语言的特点都接近……甲骨文和《易》都在深层系统地表达古人对天地与人生规律的认识”③★★★。过去那种将八卦原型与甲骨占卜法视为两种相互独立的占卜法,认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看法需要重新审视,二者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关联。
甲骨占卜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历史转折,它标志着★★“初始的神灵思想”转向以宇宙某个代表物“占卜为依据的理性思想”★★★,这一转变在两方面乃是决定性的:“首先,在信仰上★★,龟占把占卜从通过祭祀乞知神灵善凶的初始参照中分离出来……这正是中国占卜理性与通往神学之道分叉而走向阴阳五行学的转折点。其次是在技术制作流程上,龟甲占卜法在方法上具有实验性……占卜师们成为完善这一投射的专家,并将构成此投射的兆文程式化,使之成为几乎是科学性的占卜。”(《占卜与表意》,第15-16页)显然★★,汉学家对于远古中国的“实用理性★”给予了过于科学化的阐释,科学占卜并不存在,但是占卜里所蕴含的科学萌芽与理性内蕴却是实存的。其实★★★,这种转折的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巫史传统★”★★,这种传统带来的天人沟通才是中国远古思想没有走向神学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汪德迈所见的通向了实乃后发的阴阳五行学。汪德迈判断的缺憾在于,既把中国化的思想根源与后来思想之勾连说得太晚★★★,又把西方式的科学思想在中国说得太早。
孔子与巫术传统到底是什么关系?据马王堆帛书《周易》的《要》篇记载,夫子本人明确表示★★★:
《要》篇记载了弟子对孔子态度前后不一的质疑。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惪(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早年教育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无德行的人才趋于神灵★,“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缺智谋的人才会频繁地卜筮。夫子却自认为这与晚年好《易》并不矛盾★★★,事实上也是如此,德先卜后与德在卜前的晚年主张,与他早年“德行★★”在“神灵”之先、“智谋”在“卜筮”之前的立场是一致的。
②张政烺《试释周初书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卜》,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从人类智慧发展的高度来看,这是从“象征符号体系”到“数字符号体系”的飞跃,一般认为这构成了一种“数字理性”★★★,但是汉学家认为:“随着蓍占★★★,人们从占卜学的形式(规以卜兆形)类比思辨进入抽象程度更高的数字思辨,思考奇偶数之分的营数。初看上去,这是通过对龟卜术的形态——逻辑理性的超越★、达到的数学理性而完成。而事实绝非如此。取自《易经》的数卦法与龟卜占用的是同一种形态——逻辑。★★”(《占卜与表意》★,第59-60页)的确,这揭示出龟卜占与数卦法的历史关联★★,但是向数字符号的跨越并没有达到彻底抽象化的数字理性高度,其中始终融汇了感性的形式与内蕴,这就涉及“占卜理性★”之外中国古人所具有的另一大智慧源泉——★“占卜感性★★★”。
我们由此切入《易》孔关系,从巫史传统的角度审视其关联。如果帛书《要》篇能在一定意义上显露出孔子本意的话,那就说明,孔子对《易》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孔子在晚年以前视《易》卜筮之书,认为它是和德行、智谋相悖的,其不好的态度十分明显……只有在孔子★★‘老而好《易》’★★★,认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知其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甘冒★★★‘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风险时,才有可能发出‘学《易》可以无大过★★’的感叹,才能产生‘加我数年’的愿望★★。”(12)
如此观之★★,孔子可以被视为“占卜德性”的创立者,他对“史巫之筮”采取“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的态度也就易于理解了,尽管对史之筮和巫之筮也有所向往,但用《易》却大异其趣★★。《要》篇记载了孔子占筮的具体情况,弟子问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夫子答曰:“吾百占而七十当。★★★”需要强调的是,夫子是以★★“占卜德性”的立场对待占筮,明言“吾求其德而已”,这实际上是★★★“以《易》求德”★★,因此未囿于巫史那种低级的感性和理性层面,而是由此生发出对德性的更高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说,夫子与巫史同一途径,所归却差之远矣★★★。
笔者认为,从“幽赞”而★★“明数”,的确达到了★★“占卜理性★★”,而且是数理化的理性,同时亦以感性形式呈现。“幽赞★★★”更多彰显了古人的★★★“占卜感性”★★,其中也包孕着理性成分★★。如此观之,以“占卜感性★★★”为主的★★★“赞”走向以“占卜理性★★”为主的★★“数”的同时★,也开始从“巫”中走了出来,因为巫在此已经被理性化了,而且被一定程度地数理化了,这就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尽管此★★★“数”仍为筮占所用,排列“数”的呈现方式仍包孕着感性组合的表象功能,但是数理化的倾向已不可逆转★★★。
孔子更是一位以知贯行者★★★,所谓“欲仁至仁★”,显然来自“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尔》),仁之道不远人也★。从★★★“知《易》行《易》”到“欲仁至仁”,大概可以区分《周易》智慧与孔子思想之别★,但这只是个非常粗浅的大致说法。晚年好《易》的夫子,究竟如何理解《易》与仁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巫史传统★★★”的角度出发来重释《周易》与孔子的关联★,进而发现《周易》对于中国人的★“情理结构”之历史建构的深层影响。
①[法]汪德迈著,金丝燕译《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简称“《占卜与表意》★★”与页码★。
帛书《要》篇曰“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这一赞一数★★★、一巫一史,恰将《易》与巫史传统勾连起来。这个论述非常关键★,因为它说明了夫子究竟如何延续了★★“巫史传统★★”,又何以走出了“巫史传统”,而且,巫传统与史传统也被分别加以处理。一般人会认为,巫之《易》主“幽赞”,史之《易》主“明数★★★”★,夫子之《易》主“达德★★”,似乎有着不同的知《易》与用《易》的方式。其实,巫传统与史传统并不能决然分殊,★★“史”作为一种历史角色,其本意源于用动物甲骨占卜后在骨上着颜色的特定身份的人,他们曾是参与卜筮的记载者。巫人★★★“幽赞★★★”,张政烺的释读为★“赞,解说。幽★★,深微★★”(《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第167页)★,这种“赞”是感性显现,但是在巫人的★★“解说”当中又有理性化的阐明★。虽说巫人难达于数,然巫人用数却史有记载,史者也在史上从于巫★,巫与史难分,但二者都未能★“达德★★”。孔子则让“德★★★”从巫史中脱胎出来,这是孔子解《易》的真正拓展之处。
“幽赞—明数—达德”是孔子把握《易》的内在逻辑的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通过知《易》而行《易》,夫子最终要达到的是“仁守”而“义行”★★。甚至可以将知与行拆开来说:“知《易》”要达乎“守仁★★★”★★,“行《易》★”则要达乎“行义★★★”★,如此★★,对《易》之知行也就达到了“仁义”★。这个求仁得义的过程★★,笔者称之为对★★“占卜德性”的寻求。向这种更高的“占卜德性”转化,正是儒家得以超出★★“巫术传统”的根本原因。
(13)吕相国《帛书〈易传〉理性精神内在架构蠡测》★,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5期。
从“幽赞”“明数”到★★★“达德”★,后世论者认定其发展逻辑是一种历史的逻辑★:“赞★★”之用作为《周易》的原初之用,是逻辑起点;经由与人较远的★★“自然理性”,亦即“数”★★,归结为与人德性直接相关的★★★“人文理性”,亦即“德”。(13)这样做的前提是★,★★★“赞”与“数”显现的是天道,而“德”显现的则是★★“人道”,同时意味着,从★“赞”开始,先是达到★★★“数”的自然理性,进而达到“德”的人文理性。然而问题在于,无论“赞★”还是“数”都不只是先天的自然理性,“幽赞”的解说深微乃是人为的★,而“明数★”更是后天的理性抽象出来的,“数”实乃人类的“发明”而不是对自然的★★“发现”。况且★★,这种自然与人文理性的二分★★★,尚未得见孔子于先天与后天、自然与人文之间本然融汇的状态,也未看到自然与人文两种理性当中都蕴含着感性的成分,中国人的智慧就在于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与统一★★。
Copyright © 2012-2018 公海赌赌船官网jcjc5500,710jc7公海,公海jcjc5500网站 版权所有
电 话:0898-08980898 手 机:13877778888 传 真:0000-0000-00 E-mail:admin@Your website.com
地 址:广东省清远市

扫码关注我们